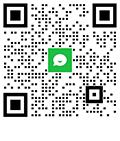剛接過這枚《山居即景》,手頭一沉,這是一塊極好的田黃凍,390克,幾近八兩的重量,捧在手裡很是壓手。作為一個(gè)癡迷壽山石的玩家,上手這樣的田黃,哪裡會有不激動(dòng)的?這塊田黃刻的也是極好,是石卿(郭懋介)先生的作品,雕刻于1998年。如(rú)何好法?除了畫意、刀法這些很見功力的表現外,這件作品還流露了充沛的情感——那種如(rú)沐春風般歡悅的情緒洋溢于畫面的每一方景色。這也的确是一件描繪初春時節的作品。沉浸在石卿先生的觀想裡,仿佛我們這些看客也已置身其中(zhōng),成為這方景緻中(zhōng)的某個(gè)人物。
像這樣能夠引發觀者代入感的作品在壽山石雕中(zhōng)還是不多見的。大多數石雕藝人隻能表現靜止的畫面,因為他們臨摹的就是靜止的事物;能夠捕獲瞬間的動(dòng)态并在作品中(zhōng)表達出來,已擁有難得的觀察力和(hé)表現力;而情感的融入最是困難。畢竟石雕不似書畫。書畫隻要掌握紮實的技法,情緒就有可(kě)能通(tōng)過筆墨瞬間迸發;壽山石雕的創作則慢上許多,每一刀的刻劃都需要冷(lěng)靜和(hé)嚴謹,尤其是薄意雕刻,往往作品還未完成,情緒或許已經平複。我們常說,壽山石雕是“戴着鐐铐的舞蹈”,意指壽山石天然的色彩、紋理和(hé)瑕疵常常會限制雕刻家的發揮;而石雕藝術(shù)若要表達情感則更為不易,技法嚴謹的施展所耗的時間必然會将情感逐漸消磨殆盡,從這個(gè)角度來看,雕刻本身即是戴着鐐铐的舞蹈。石卿先生顯然是一位能夠将自己情感從容表達的雕刻家,在這件作品裡,他将飽漲的熱情緩緩地釋放,不疾不徐的向我們描繪初春的田園山水,他就像作品中(zhōng)坐(zuò)在山石上清談的老者,仿佛在訴說他記憶中(zhōng)的美好,又隐約覺得,這裡就是他内心深處的向往,直到我們流連忘返之際,這幅薄意圖卷也勾勒完畢。石卿先生于畫中(zhōng)的崖壁題款說“戲作山居即景書于仙山下(xià)”,令人不覺莞爾,可(kě)是也莫明的有些失落,景色已經遊覽完畢,卻依依不舍,那種心情就好像踏青玩瘋了的孩童絕不肯回家一般。
在石卿先生面前,我這年齡算作孩童也不為過。我與石卿先生有過一面之緣,那是2011年,也是初春之際,去他家中(zhōng)采訪。那時石卿先生已經87歲高齡,由他的兒子(zǐ)白羽(郭卓懷)先生照顧起居。聽說年輕些時,石卿先生非常健談,當時卻已不怎麼能說話,訪談也由白羽先生代為回答,石卿先生就坐(zuò)在那裡,眼裡含着笑意,默默地看着我們,偶爾緩緩的燃上一根煙,偶爾緩緩的插上半句話。采訪末了,我們這群小字輩為石卿先生拍照,借機與他合影留念,石卿先生也樂(yuè)呵呵地,任由我們折騰。此後就再未見過先生,看得出他喜歡熱鬧一些,可(kě)也真的不忍去叨擾他的生活。
回想這段經曆,總會感慨人老之後的那種淡泊和(hé)質樸,這卻也不是誰人都能夠擁有的。于工作的緣故,我常有機會能夠上手石卿先生的石雕作品,也常能感受到石卿先生于創作中(zhōng)流露的情懷。從某種意義上說,石卿先生所選擇的題材,不論是佛道仙凡還是漁樵耕讀,抑或是田園山水,于現世當中(zhōng)都擁有超然物外的含義,在他的刻刀下(xià),也的确擁和(hé)光同塵、物我兩忘的意蘊。他的圓雕人物就像在刻劃他自己,親和(hé)并具有感染力,有着佛家博愛的關(guān)懷;他的薄意透着與自然的親近,頗有道家隐逸之風;而他一生的經曆,卻是格物緻知、修齊治平的儒家典範,正如(rú)南懷瑾所說“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的人生哲學,這或許也是石卿先生所追求的境界吧。隻是今春五月(yuè)石卿先生這一去,壽山石雕刻藝術(shù)一代大家隕落,今後怕是很難見到這樣的風骨了。回頭再端詳這枚田黃,又有了一些黯然的意味,不免有些感慨:山居即景今猶在,不知石卿已何往。(來源:集珍文(wén)化 文(wén)/李玉山 圖/福建東南拍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