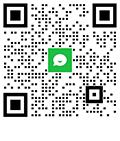無論什麼事,似乎一旦有了中(zhōng)國文(wén)人的介入,都立刻顯現出與衆不同的審美趣味來。或者說,能夠有閑情餘韻将美學和(hé)精神意象充分落實于生活的每一處,從起居飲食到詩書畫印無不飽含悠久的文(wén)人美學的傳統。
當這樣的審美趣味被融入生活本身,似乎最為普通(tōng)的物件都能瞬間流露出難以言說的動(dòng)人風骨。其中(zhōng)最為著名的例子(zǐ)大概非文(wén)人畫莫屬了,從魏晉時期的萌芽,到北宋時形成與院體畫并行的“能畫不求售”的文(wén)人畫基本樣式,再到元代的發展高峰,最後乃至于明清的鼎盛時期,文(wén)人們常常通(tōng)過筆墨寄情于山水,書寫自我的胸懷與情思。如(rú)同“詩以言志”和(hé)“文(wén)以載道”一般,畫中(zhōng)的山水草木也并不再是單純的風景,“山之高峻、水之澄明、蘭之幽潔、竹之清高、梅之傲骨……”,這些入畫之物往往寄寓了文(wén)人士大夫階級本身的道德品質和(hé)理想追求。這種撲面而來的“書卷之氣”形成的審美趣味并不随着朝代的更叠而改變,卻愈發地在文(wén)人士大夫階級中(zhōng)形成傳統,不斷地得到發展與更新。
這樣的發展,達到了淋漓盡緻的境界之後,必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是嫁接到其他藝術(shù)之中(zhōng)。文(wén)人畫與工藝美術(shù)的互融互動(dòng),推動(dòng)了新的雕刻技法的誕生——或如(rú)雲煙般影影綽綽,或如(rú)山巒般重重疊疊,圍繞石材表面所做的極為纖細淺薄的雕刻,既有浮雕的立體感,又充滿了中(zhōng)國畫式的意境和(hé)構圖,因此被稱作為薄意。
那麼究竟何為“意”?
《春秋繁露》有“心之所謂意”,即意由心生,單純的觀感隻能稱為“形”,而通(tōng)過“形”所體味出來的才能稱之為“意”。薄意之“意”當取此引申義,乃是體悟、感覺的意思,類似于“意境”、“意趣”。值得一說的是文(wén)藝作品或者自然景象中(zhōng)所表現出來的情調和(hé)境界,明代朱承爵在《存馀堂詩話》中(zhōng)對于詩的意境作如(rú)此評論:“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唐人張彥遠(yuǎn)在《曆代名畫記》中(zhōng)則如(rú)此評論“畫意”:“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大意而歸乎用筆。”
與詩畫中(zhōng)的“意”本質共通(tōng),壽山石薄意雕刻中(zhōng)“意”的境界也必須在于此,它不僅僅需要給觀賞者呈現出幾寸印體上所能展示的那些雕刻,更需要表達出雕刻者自身所寄托其上的審美構思乃至道德趣味。而且,這種構思趣味也必須讓觀賞者能夠心領神會,就是畫面的理性與雕刻者的感性渾然一體、情景交融,雕刻者與欣賞者相互溝通(tōng)的境界與狀态。現代著名閩籍藝術(shù)家潘主蘭先生對薄意也有過精彩的總結,其言:“薄意者技在薄,而藝在意,言其薄,而非愈薄愈佳,固未能如(rú)紙(zhǐ)之薄也;言其意,自以刀筆寫意為尚,簡而洗脫且饒有韻味為最佳,耐人尋味以有此境界者。”應該是對壽山石薄意雕刻技法的極恰當評價。
可(kě)以說,自薄意技法誕生開始,它就再難與文(wén)人畫的意境分離(lí)了,因此要想詳細說薄意之“意”,就不得不先從文(wén)人畫的審美情趣處說開來。唐代張彥遠(yuǎn)的《曆代名畫記》有這樣的一段話:“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闾閻鄙賤之所能為也。”晚明畫家董其昌在他的文(wén)集《容台集》中(zhōng)這樣追溯文(wén)人畫一脈:“文(wén)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範寬為嫡子(z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家黃子(z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wén)、沈則又遠(yuǎn)接衣缽。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李大将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文(wén)人畫雖然在唐代王維便已經有了萌芽,但是到了明代才有了明确的定義。所謂“文(wén)人畫”,與其他畫最直觀的區别就是它的創作者原本是擅長詩文(wén)的文(wén)人士大夫階級,他們将表現、抒情、寫意的詩文(wén)結合入本應該偏于再現、理智、寫實的畫中(zhōng),每一道筆觸都充滿了書法意味上的氣勢與韻律,每一道線條都極具節奏感,成為抒發胸臆的載體。湯垕在《畫論》一書中(zhōng)說到的“古人最以形似為末節……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後形似……遊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kě)以形似求之”,狀物不求形似而求神韻,物象既是畫家自身情感的載體,又是其筆墨運用的載體,畫面充滿詩意。在注重主觀感受的前提下(xià)進行寫意,畫面強調平穩、和(hé)諧、秀逸的神韻。而神韻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求形似卻最終因氣韻生動(dòng)而自然有了形似的感覺,韓拙在《山水純全集》中(zhōng)曰:“凡用筆先求氣韻,次采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得于其間矣。”也就是說,文(wén)人畫首先要追求的就是氣韻生動(dòng),然後才是布局構思,那麼“形似”便自然而來,即“心随筆運,取象不惑”、“意在筆先,畫盡意在”,使得内心與自然融為一體,達到借物抒懷的目的。
“畫之為物,是性靈者也,思想者也,活動(dòng)者也……所謂藝術(shù)者,即在陶寫性靈,發表個(gè)性與其感想,而文(wén)人又是其個(gè)性優美感想高尚者也”。他們追求的是繪畫的“氣韻生動(dòng)”,正因為是“思想者也”,所以文(wén)人在繪畫時必定要借物抒情。在選擇繪畫對象時,往往所選擇的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氣質正是文(wén)人追求或者向往的氣質。不僅如(rú)此,文(wén)人畫家還會以自身的畫法、構圖乃至筆觸來刻意地誇大對象顯示這種精神氣質的某些特征,借此将胸臆表露于衆。随着這種刻意誇大或者移情,物象被畫得“像不像”似乎已經不再是文(wén)人畫所追求的了,作品中(zhōng)的形體不過是用來表達作者精神和(hé)情感的載體而已,就如(rú)倪瓒所言“餘之竹聊寫胸中(zhōng)逸氣者,豈複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技久之,他人視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餘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可(kě)見文(wén)人畫家所希望達到的境界與畫院畫家或者民間畫家并不相同,他們在創作的過程中(zhōng)注重借物抒情,即使筆下(xià)的“物”不再是真實之物的複制甚至相去甚遠(yuǎn),卻因為帶有了畫家本人的“真情”而顯得更能打動(dòng)觀賞者的心,引起共鳴。中(zhōng)國文(wén)人畫中(zhōng)常出現的幾種物象都帶有特别的意義,譬如(rú)竹之重節虛心、梅之傲骨淩寒、蘭之孤潔脫俗、山之高峻堅忍、水之阻隔溝通(tōng)……以至于某些與物象有關(guān)的場景,也有着固定的意義與氣質,它們在經曆了幾百年的反複創作之後,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某種氣質或精神的代表,并不單單隻在文(wén)人畫家圈子(zǐ)中(zhōng)流傳。
這些特定的物象和(hé)情境,也被壽山石的薄意雕刻所借鑒升華,從而産生了特定的畫面創作。自薄意誕生至今,保留或者傳承下(xià)來的傳統題材有很多,曆史典故和(hé)名流轶事的有與蘇轼、黃庭堅和(hé)佛印有關(guān)的的《赤壁夜遊》、與陶淵明有關(guān)的《東籬采菊》、與孟浩然有關(guān)的《踏雪(xuě)尋梅》,與李白有關(guān)的《春夜宴桃李園》(原畫為明代畫家仇英所作)、與西晉竹林七賢有關(guān)的《竹林七賢》、與王羲之有關(guān)的《羲之愛鵝》、與米芾有關(guān)的《米癫拜石》等,詩句意境的有《牧童遙指》、《桃園洞天》、《對影成三人》、《春江水暖》、《漁歌歸晚照》、《風動(dòng)鳥聲噪,山深竹影寒》、《數點寒梅天地心》、《夜半鐘聲到客船》等,儒釋道三家的有《歲寒三友》、《四君子(zǐ)》、《八仙過海》、《紫氣東來》、《達摩面壁》、《和(hé)合二仙》等,以上這些都是文(wén)人畫中(zhōng)常見的、從實在的人與事或者已有的詩句故事中(zhōng)化用而來的題材,而文(wén)人畫中(zhōng)獨創的情境也常常被用在薄意雕刻中(zhōng),如(rú)《攜琴訪友》、《秋山行旅》、《寒林幽居》等等,還有一些從文(wén)人畫中(zhōng)脫出的就是各種花(huā)草動(dòng)物了。
我們從當中(zhōng)可(kě)以發現,以上這些雕刻題材多出自文(wén)人畫,本身也具有和(hé)文(wén)人畫同質的對精神氣質和(hé)情感抒發的需求;但如(rú)同明代中(zhōng)後期繪畫商(shāng)品化蔚然成風,有畫家不願多揣摩創作而是一味進行摹古,重複構思,甚至出現了為了迎合富商(shāng)大賈的口味而不顧個(gè)人感情之無所發,為了金錢而作畫的風氣一樣,薄意雕刻也難免必須經曆這樣的過程。何況與文(wén)人畫不同的是,有官職的文(wén)人士大夫階級顯然可(kě)以将作畫當做一種自我消遣的方式,即所謂的“能畫不求售”,但壽山石雕刻并不是和(hé)文(wén)人畫等同的純粹的自我消遣的方式,除了石材本身具有較高價值導緻雕刻家們難免為此锢足以外,壽山石雕刻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出售并為自己帶來相應的價值,因此那種受到文(wén)人青睐又被大衆廣為接受的題材就能夠長久不衰,并且被重複套路(lù)式地雕刻于壽山石上。這就造成了一個(gè)讓我們不得不引發重視的問(wèn)題,這些原本被認為是“脫俗”、“高雅”、具有“文(wén)人審美趣味”的薄意構圖與題材,在長久的重複雕刻過程中(zhōng)也開始漸漸“日常化”、“世俗化”,使得薄意雕刻中(zhōng)的“文(wén)人畫”意味逐漸變淡。
這種重複套路(lù)式的摹拟之風在中(zhōng)國畫中(zhōng)也有先例,對此畫論學者并非一味地采取批評摒棄的态度。其中(zhōng),郭熙就認為作畫不妨學習古人,但關(guān)鍵是不可(kě)限于一家,千篇一律,他在《林泉高緻》中(zhōng)指出:“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鐘、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并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古人作品之所以得以流傳下(xià)來,必然有他的獨到高妙之處,若是能先将各家的長處融會貫通(tōng),并且有了自己的特色,便能夠自成一家。郭熙在這裡強調,雖然最初可(kě)以進行重複的模仿,并且這種模仿确有裨益,但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是能夠創造出屬于自己的風格。繪畫不可(kě)能完全不借鑒古人,但學習古人不應該機械地臨摹,而應當得其神、通(tōng)其意。
薄意雕刻也是相同的道理,由于薄意雕刻本身從誕生到現在也不過短(duǎn)短(duǎn)的三百餘年歲月(yuè),自然要從其他的藝術(shù)比如(rú)竹刻、中(zhōng)國畫、書法甚至是古詩詞上汲取養分、借鑒神采。這也是必須要經曆的過程,重複着某些固定的物象題材與布局構圖從某種角度而言也是一種積澱的過程,隻要有了一定程度的堅實積澱才可(kě)能進行進一步的創新,否則便是“無源之水”、“空中(zhōng)樓閣”。但同樣地,重複題材這種做法若沒有自己的想法與構思在其中(zhōng),隻知道埋頭生搬硬套,則往往容易産生毫無新意、死氣沉沉的結果。袁宏道曾經提出“故善畫者師(shī)物不師(shī)人,善學者師(shī)心不師(shī)道”的觀點,意思是善于學習借鑒的人應該從自然之物中(zhōng)獲得靈感,應該學習的是他人的精神而非具體方法,這才能夠從古人中(zhōng)獲得啟發,創造出“學古而不泥古”的作品——這就是工匠(jiàng)與藝術(shù)家的區别。具有豐富雕刻經驗的薄意大師(shī)也往往能夠從舊題材中(zhōng)進行自我發揮,恰到好處地創作出獨具心裁的作品。不同的手法不僅是創作者自身不同風格的表現,甚至還是創作者對于題材不同角度的理解,因此并非傳統文(wén)人題材便必定落入俗套,“橫看成嶺側成峰”,隻要創作者對于題材有了屬于自己的獨特理解,将屬于創作者的新生命新精神注入到原本的老題材中(zhōng),就會顯示出别具一格的新意來。
在三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zhōng),薄意雕刻在與文(wén)人畫的互動(dòng)中(zhōng)受益良多,但是也逐漸有了自己的題材特色,以真正民俗化的物象入題創作,産生了民俗物象藝術(shù)化。當創作者提取了常見的生活意象并進一步加工之後,民俗物象也能夠充滿文(wén)人氣,成為書房(fáng)案頭的珍玩清供。可(kě)見作為鑒賞者不能因為作品的題材生活化而輕易貶斥一件作品的價值,“源于生活”的題材隻要能夠最終“高于生活”就是好的作品,并非日常的事物便不能具有藝術(shù)氣息和(hé)審美趣味,關(guān)鍵還是雕刻家的構圖到雕工的創作手法和(hé)表現形式的問(wèn)題。這些受到世俗歡迎的題材,随着社會平民意識的增加和(hé)壽山石受衆的擴大,越來越多地呈現于壽山石雕刻特别是薄意作品中(zhōng)。
藝術(shù)創作就是如(rú)此,它常常經曆着從生活到藝術(shù)再成為藝術(shù)定式,繼而由生活再次突破藝術(shù)定式的過程。也是在這樣的過程中(zhōng),藝術(shù)殿堂得以不斷地添磚加瓦,從而逐漸地豐富起來。所以說,薄意追求的是文(wén)人美學的神韻,而不必禁锢于題材和(hé)内容,民俗的題材用恰當的方式也會呈現高雅的情趣。(來源:集珍文(wén)化 文(wén)/唐穎 圖/福建東南拍賣)
(福州市新權南路(lù)9号)
(福州市楊橋東路(lù)19号衣錦華庭壽山石文(wén)化城二樓)
(福建省民間藝術(shù)館正對面)